问鼎娱乐-门兴格拉德巴赫训练课后刷新队史纪录,志在足总杯名次提升,信心回归,心理建设被强调(拜仁对门兴格拉德巴赫在线观看)
2006年,画家周思聪(1939-1996)生前挚友、记者马文蔚,整理了周思聪1980-1992年写给她的142封私人信件,结集为《周思聪与友人书》,在征得周思聪子女同意后,交由大象出版社公开出版。
周思聪(左)与马文蔚在画室,1987年。
这些通信的时间,正是周思聪摸索创作矿工图组画、彝女系列,取得为人瞩目的突破性进展时期。自然,这创作方面的一些事情,在通信中有不少提及。不过,作为“闺蜜级”通信,其中包含的信息当然就不仅止于这一方面,而是涵盖了一位“人到中年”(对于周思聪五十七年的人生来说,是特别容易让人发扼腕之悲的“人近晚年”)的艺术女性,在社会生存中曾经遭遇的方方面面。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艺创作挣脱铁律束缚的那种兴奋、变动与紧张,而且可以了解周思聪的为人处世、家庭生活,特别是她“这个人”精神世界中“十分孤独”和感怀“春天”的那一面。
“春天”之于“孤独”,意味着什么?周思聪总是经意或不经意地在信中寄予着她对“春天”的脉脉思念和感念。譬如:
“北京这满载风沙的春天,又诱人,又恼人,但毕竟是春天来了”(1981-3-15)
“收到你的信时,春树刚刚透出轻柔诱人的淡绿。”(1981?-4-9)
“北京的春天短暂得来不及品味,大风刮得眼睛还没睁开,她已经去远了。”(1981?-4-22)
“春天的气息,使我心情舒畅起来,更主要的是见到你的信竖在居委会窗户里。”(1982-2-18)
“春天里相聚格外喜人。”(1982-3-15)
“似乎又要听到春天悄悄的脚步声,人的情绪也会随之舒展。”(1983-2-27)
“还是想去春游一次。”(1983-4-4)
“春已悄悄离去,我却什么都没感受到。……带着这一切,连同我心中的春意都带走了,连一个梦都没有留下。”(1985-4-21)
“天气再暖些时,你来春游一次吧。”(1986-3-1)
“这个春天又是在病房里。”(1988-2-29)
“春天又悄悄向我们走近了。”(1991-2-5)
人们常说,春天寄予着希望。通过这些信件,我们可以看到像周思聪这样一位性格沉默内向、生活苦重忍耐、内心为孤独所系的艺术女性来说,这希望更多意涵着那种对真心相待、无拘无束的精神交流的渴盼。春天,在她这里,无疑是对精神交流的比喻和象征,也无疑是她那份连自己也说清不清楚怎么回事的孤独所弥足珍视的呼吸。实际上,这种精神呼吸即便是丈夫卢沉也未见得能全然寄予,尽管他问鼎下载们生活中相濡以沫,彼此之间也颇为默契。但憨厚的卢沉却很少关心周思聪的感情,很少过问她想什么,有时他们“一天也说不上十句话,有时突然谈得很多,准是学术问题的讨论。”(1982-4-4)学术问题的讨论自然是夫妻间重要的精神生活,但毕竟不是精神生活的全部,而在讨论学术问题之外,周思聪所希冀的精神生活也不仅限于不定期的约朋友一块儿见面聚聚,她更希望那种相互之间平等真诚、开诚布公的忠告、开导、指引、批评和分享。而这在他们夫妇俩中间之所以被挂起来,“常常是沉默”,要么是“从对方的眼光中窥探一切,无须多说,什么都明白”(1981?-12-29)的结果,要么是卢沉避免触动周思聪“伤痛”的谨慎之举,但这又恰恰让周思聪觉得“冷漠”(1982-4-4)。
现在看来,作画之外,给挚友写信——有时周思聪写信的环境和条件如同战地画速写一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是她愿意“倾诉”自己所见所识所思所想的唯一管道。幸亏在她的人生中能邂逅给予她精神呼吸的闺蜜!现实生活中话少得让人觉得冷漠和害怕的周思聪,在这个管道里以诚相待,真情告白,绝不遮掩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更不假装和虚伪!她是将“信任”视为标记人际质量的那一类人,这在她看来也似乎是“本性难移”了(1982?-3-23)。
在这些见心见性的精神世界的沟通与交往中,有不少文字记述和分享了周思聪阅读文艺作品的经验与心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她的精神活动、追求和品味。周思聪爱读书,这一时期的她关注文艺思潮动向,特别是对文学作品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攫取,虽然限于条件她的阅读还不太够,到不了读书千万卷的程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鲜活而有质量的灵魂怎样欢度着属于她的“春天”,并且对我们更全面和立体地研究周思聪这一时期在绘画创作上发生的取向亦有极大助益。
周思聪的这些信似乎表明她随时都在用心学习和思考,其中也不乏反省以及对自己的解剖,而她的文风也像她绘画里的那些线条一样,有质感。
这里摘选数封并配以插图,以尽纪念之意并满足个人在研究上知人论世之需。
文蔚:
书是今天(3l日)收到的,两小时之内我已看完一遍。
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
干校生活,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极能理解她的每个细节描写,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人是那么懦弱,又是那么坚强。那么容易被残杀,又是那么难以被压垮。卢沉从干校回来时,曾说起过他去拉煤的情形,他被当作当然的壮劳力,时常被派出去为连队拉煤。那么沉重的煤车,泥泞的陡坡,漫长的路;若在平时真是难以想象他能对付得了。每当他精疲力竭倒在路边时,第一个感想就是:一个人,一个有知识的人,像蚂蚁一样没有价值、渺小。他的一个学生,肺结核已是两肺空洞,还须去锻炼。第一天就经不住旅途劳累,当晚死在他身边(他与他同睡一个炕)。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为他着想吗?问鼎app包括他的双亲在内?而想又能怎样?只会使那揪紧的心更加疼痛而已。
我去干校时正怀孕,可以说儿子未出世,他已在干校毕业了。当时留守的人都是出身好或本人是工人的。我们那个单位所谓工人阶级,就只有传达室的和司机了。好心人都劝我争取留守,无奈不够条件,况且又有“五一六”之嫌。不过我毕竟是幸运的,大家都暗中照顾我,特别是老大姐们,时不时地嘱咐我。尽管如此,我终于还是出了问题。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不小心用力不当,破水早产。当地连个卫生站都没有,军宣队也着了急,打了许多电话,从人艺要了车,赶到干校,拉到城里六院。孩子只有七个多月,生不下来,医生气呼呼地说:羊水都流光了,怎么生?这时我才意识到危险是存在的,但人到了这种时候并不怕了,听天由命而已。陪同我来的女同志与医生商量“剖腹”,而医生却不同意,毕竟她是有经验的。痛苦了三天之后,竞生了下来,只有四斤多重,就是现在同我差不多高个子的儿子。当时,他爸也在干校,并不准回京探视。指导员说,生孩子没什么稀罕,不必请假。的确,没什么稀奇,所有的妇女都会生孩子。一个同事的父亲去世了,包括路途只允了三天假。返回干校晚了两小时,作检讨,何况生孩子呢?卢家父子相见时,孩子已经一周岁了。
产假倒是没有克扣,五十天一满,立即返回干校。喂奶?不行。军宣队说了,不吃人奶的孩子一样胖。早产的孩子又吃不到母乳,做老人的能不揪心?婆母当时七十八岁,真正的一老一小。夏天,牛奶很容易变质。不能冷又不能热,孩子体质又弱,把老人折腾苦了。我在干校也难熬,想到孩子奶水就像要胀破一样。每天用杯子挤出来倒掉。幸亏周围都是过来人,传授经验,没有憋出奶疮。好不容易盼一次休假,看到孩子弱小的身躯,我难过、我恨,却不知该恨谁。
后来听到许多人谈到他们各自的干校生活,相比之下,我们的干校还是天堂呢。
……
思聪7,31[1982?]
文蔚:
你的诗我喜欢。它没有耀眼的词藻,像一条漫流的小溪。不华丽、不造作,是那样自然地流过来的。我觉得诗、书、画都应当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它应当是没有一条预定的路线,而恰恰又是按照必然的路线流过去。正像溪流一样,而非人工的水渠。我常喜欢拜读孩子的画,他们没有要讨人喜欢或怕人耻笑的种种顾虑,一心一意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它真挚,就必然可爱,尽管拖鼻涕、开裆裤也可爱,而我自己的画上则各种雕琢的痕迹太多,条条框框太多,使我不能自由地抒发。
周思聪爱子卢悦幼时涂鸦照
最近《矿工图》的第六幅——《遗孤》,刚刚完成。我每画完一幅画,都像打了一次败仗,我没有别人所体验过的那种“胜利的欢乐”。多么想体验一次呵。
烦躁,想发火的时候,我也常有,那常是在失去了目标的时候。
……
今天是青年节,它已不属于我们了。
思聪5,4[1981]
文蔚:
《傅雷家书》从《文汇》月刊9期上翻到了。这位清醒的父辈,“中国儒家的门徒”,他所谈及的许多问题,使我感到,“人”的质量高低差异之大。这些都写于1954年,如果从那时起,人们都能如此正常地看问题,将是怎样的可喜?现实是,愚昧是那样容易地蔓延着。
真正的艺术家都应具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同时也需有外科医生的“冷酷”,这冷酷正是由于爱得深切。而这深切的爱却不能被接受,甚而将其误解,这是艺术家的悲哀,更是患者的悲哀。这种情形之下,许多所谓的艺术家就干些修眉毛,涂唇膏的行当,只需把握一种雕虫小技,吃遍天下了。这也是他们的悲哀。
……
《文汇月刊》,1981年第9期。
《文汇》9期封面的大美人儿是昆剧演员梁谷音。梁谷音是好演员,可这个封面怎么样?他们编辑大人们想把我也照此办理,我当然要和他们作对。难道我在中国妇女英文版封面上当了一次卖牙膏广告还嫌不够吗?
……
再谈。
思聪10,9[1981]
对一个作曲家说来,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失去信心。音乐,以及整个艺术,不能是冷酷的嘲讽。音乐可以是辛酸的,失望的,但不能是冷酷的嘲讽。在这个国家,人们喜欢把嘲讽和失望混为一谈,假若音乐是悲剧性的,他们会说它是嘲讽。我不止一次遭到指责,说我是在冷酷地嘲讽,而且,顺便说一句不止是政府官僚这样谴责我。失望和嘲讽是不同的,正如厌倦不同于嘲讽一样。一个人感到失望,那意味着他仍然对某种事物怀着信念。
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认为一切都在前面。我们急匆匆地看见什么便抓住什么。我们的心灵里塞满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但是,三十岁后,我们的心灵里又塞满了灰色的无聊的东西。
要在我们肮脏的时候爱我们,因为当我们一身干净的时候,谁都会爱我们的。
公民们,别相信人道主义者,别相信先知,别相信名人——他们会为了一分钱而愚弄你。自己干自己的事,不要伤害人,要努力帮助人。不要想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
当你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后面的东西:情绪和音乐。
无论英雄还是恶棍,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不黑也不白,是灰色的,模模糊糊的灰色。我们时代的基本冲突就发生在这模糊的灰色中间地带。
文蔚:
上面是我抄录的打算寄给你。接到电话后,我改主意了,把书带给你。这本书,你会比我体会深切得多。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并整理,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1年。
“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小学生时背过的课文,只这一段,我总也忘不了。那时当然是不懂的。中年了,才似乎懂了一点儿。只是一点儿。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如此。人们埋怨着、希望着,又失望着,但还有路可寻。如果大多数人麻木了、厌倦了,就无望了。
你抄录的梅兰芳的一段,于我很有针对性。卅年来,谁也不敢说“为自己欣赏的”,他敢。这也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艺术有信心。“自己”能代表真正喜爱他的艺术的人。
……
思聪2,问鼎国际5[1982]
文蔚:
我的信意外地保住了你书包,而且是无锡的信。这么说,这些信还在经受你翻来覆去的推敲,这使我很难为情。
书,儿时看过的不算数,是指对作品本身的理解,我同意。但我觉得,那时读的书,固然不甚解,但对于我的性情是有较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信不?特别是对于人格的高尚与卑贱,书里能告诉我许多。当然不是指一般市俗的标准。
谢冰心的文笔我也喜欢。对鲁迅我与你看法有些不同。我以为他的作品艺术感染力极强,他恰恰不能做政治家。他偏激,他搞不得政治。他又太仁慈,搞政治准倒霉。他说是横眉冷对,其实他最不善冷眼。因为他笔下的人物摄人魂魄。他的文笔平中见奇,最具中国民族的风度。我以为近几十年中,由于政治需要才把他的政治倾向极力夸大,这很遗憾。
《简·爱》小说,我还没读。一定找来读。我也要体会一下,你的感受为什么这么强烈,“文蔚为什么这么喜欢它”?
音乐,我当然喜欢。如果真有下一辈子,我将选择小提琴。音乐需要天才,我没有。今生不会有了。但是“喜欢”,并不需要天才。高尔基的《母亲》中有一句话我总记得:“女人都懂得音乐”。肖的书中也断言:不喜欢音乐的人不是善良之辈。孔子听了音乐“三月不知肉味”。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中国的绘画最讲“气韵”,就是指给欣赏者以音乐感。“抚琴操动,欲令众山皆响。”“歌”是“言”,但不是普通的言,而是一种“长言”。古人说“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声中无字,是说要把“字”取消,所谓取消,就是融化,把字化为旋律。字被取消了,但字的内容在音乐中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升华了。
我同意你的想法,听音乐,要听真正的音乐。粗俗的也不见得准是“黄色的”,许多貌似革命的,其实真粗俗。
真遗憾,我每天只能听噪音。我们的新居,卢沉命名它为“噪音楼”,我觉得这名字太白了,我称它“碎梦轩”,连一个完整的梦都做不成。买录音机的念头早已打消。我现在不敢侈想音乐,只力求能使自己适应当前的噪音楼,控制自己头脑不发胀就不错了。
“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并非是要作曲家模仿流水的声音和高山的形状,而是创造旋律以表达高山流水所唤起的情操,使人灵魂受到净化。我不求净化,却只求适应污染。看我说的多可怜,可这是事实。在噪音之中,花都不愿开,更何况人?……
再谈。
思聪3,3[1982]

文蔚:
为什么喜欢?当然不是因为它的文字技巧,或情节,你说了,它没有华丽的词藻,故事也是早就熟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心灵的共鸣。对,就是这个。我想你也是一样。一个近二百年前的信奉上帝的欧洲女子,同我们的感情共鸣,奇怪吗?一点也不。
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第一遍我不得不吞读,做不到细细品尝。但是并没漏掉一个字。许多心灵的对话,不必品味,凭直觉就已经理解了。我流了好多次泪。有些小说、电影、诗或音乐、画,都能让我流泪,甚至看见大自然的风光变幻也如此。我心里似乎深藏着一根十分孤独的弦,我说孤独,你一定能理解,它平时很难被拨动,一旦被触动我就激动不已。我不会多愁善感,也不善表达,可是容易被感动。有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简的坚强的理智引导她的感情稳妥地向着高尚发展,感情十分听从理智,丝毫也不越过理智一步。我的感情并不比她贫瘠,但它不驯,或者说是我的理智过于脆弱,它常被感情所压垮。当我的理智逐渐挣脱出来时,错误已经铸成。我丝毫也不怀疑自己感情的真实,我是不善驾驭它。
由于我是这样的人,所以也害怕别人的冷漠,特别是我所爱的人的冷漠,使我痛苦。
简是个十分自信的人。本来我也是自信心很强的,后来……我失去了自信,许多人轻蔑的眼光,曾使我战栗。你信吗?但这些毕竟不是我最在乎的,我怕的不是这个。有些人第一次接触我就对我有好感,而且都是些好人。我也愿意同他们或她们交谈。但同时,几乎就是同时,我立即害怕起来。我意识到很快就将失去他们的友爱。当他们或她们听到某些风声以后,就会立即远离我,比那些人更加蔑视我。这倒不如他们根本就别走近我好。
同你开始接触时,由于是培蒂的朋友,我知道,你不仅仅是“记者”,恐怕更属于那些想接近我的人。而且,凭直觉我知道你又是属于我所愿结交的那一种人。那我只有一种选择:……让你抉择,接近我还是远离我。你没远离我,当然是没有。我的那根孤独的弦被重重地拉了一下。为这个我流过泪。连他都觉出我有些不对劲,“怎么了,你?”他问。那次看电影,有他在,你我两人似乎有些拘束,你觉得吗?我常这样,有别人在时,我对他,就像女学生在老师面前,不太自由。他不大关心我的感情,很少过问我想什么。以前他不这样。我是说那阴云笼罩之前。我想,他是怕我多想,怕我会有任何受管束的感觉。他从来避免触动我的伤痛,这点他十分小心,可这样又恰恰使我觉得冷漠。有时我们一天也说不上十句话,有时突然谈得很多,那准是学术问题的讨论。我怕他会认为我太凡俗,所以也很少主动开口。
怎么会扯到这些上去了?你烦了吧?
《简·爱》我再留些天,这回是品味。
你说该忙一阵了,不打扰了。
思聪4,4[1982]
文蔚:
那本书中的画家,是以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为模特的。美术馆正展出的韩默藏画中有他几幅画。其中一幅题为《您早,高庚先生》给我印象极深。

萨默塞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 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
书中对他的描写,难免不带耸人听闻的色彩,即便如此,我倒也不认为他是因为自私自利,才那样不通人情的。他的思想境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与他周围那些人(以他的夫人为首,也包括那位荷兰画家)格格不入。他是赤裸裸的,而且他也能看穿别人赤裸裸的样子,所以在人世间那些仁义道德的伪装前面,他决不会自觉形秽,而别人看他就是“恬不知耻”的模样了。这也是为什么他找到最后归宿时在那孤岛上与土著人同居,感到如鱼得水的原因。那些土著人,他们也没有学会上流社会那些伪善,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纯净的,艺术最需要的就是这个。艺术永远不该去演说教的角色(而当今就是要求她作这个角色,因此就不会真诚),我倒觉得,他这样气质的人,在他弃家出走之前,竟能不动声色,显然不可理解。我不认为他脱离生活,他只是脱离他所厌恶的生活,而热情地追求着他向往的生活。对于后者他是感受极深的,这我是能理解的,只是我对我所感受到的,爱的不深,不能像他那样不顾一切。他其实并非自私,他为人类的艺术增添色彩,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从高处着眼,他伤害了(也许并非伤害)周围几个人又有什么呢?如果他顺从了这几个人,也就没有了这个艺术家,而同他们一样成了庸人。这一点,那位善良的荷兰农民画家在内心中是悟到了。因此他才那样忍气吞声的爱着他,他直觉到,他必将是伟大的艺术家。
我是不会到孤岛上去的。我们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想法不同。尽管生活中有许多事使我恨,但更多的人使我爱,即便陌路人。你信中谈到当今的青年人,我也有同感。在大城市,特别是在繁华地区,这种感觉最明显。在那些青年的脸上,本来是应该最富正义、热情和朝气的脸上,常常见到的是冷漠、无知、愚昧,甚至野蛮。那些脸也许生得端正,或许还漂亮,但一点也不生动。我相信,他们不会引起艺术家的表现欲望,原因很简单:不美。
……
我每到偏远地区、深山农舍,见到那些极少文化的庄稼人,便激动不已。
……
得收住了。你不要太累自己。你的那种病很令人担心,只有自己知道如何控制。
思聪5,3[1982?]
文蔚:
……
毕加索看了吗?不能理解,我也一样。从纯形式感要求,有些色彩也并不美。听听别人讲,油画家们似乎也说不出所以然。
1983年第6期《美术》对毕加索原作展的报道。
我喜欢展览前言旁边那张照片。具体说是照片中那些挂满墙壁、摆满地上的各种彩陶,那是非洲黑人的艺术,很美,毕氏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黑人艺术。他如果生前到过中国,也一定会将中国艺术融入其中。此人特长就是极善吸收、善变化,从不重复昨天的足迹。这大概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伟大处了。
……
思聪5,11[1983]
文蔚:
……《徐悲鸿一生》,我略翻了翻就失去了看它的勇气。我不大喜欢这样去写一个人的传记,许多情节过于具体,自然令人怀疑其真实程度。
廖静文 《徐悲鸿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
你看过司徒乔夫人写的《未完成的画》及吉鸿昌夫人写的《吉鸿昌就义前后》了吗?觉得比《徐》高得多。廖静文不是作家,这本来正是个有利条件,而她却太想模仿作家了。据说要拍电视剧了,不知会怎么样。但愿不落俗套。
……
思聪1,12[1983]
文蔚:
……
“奇文共欣赏”
你若有闲空,请看一眼《四川文学》八三年第一期,有一篇题为《朝辞白帝彩云间》的,作者就是我曾跟你提过的在四川遇到的写《达吉和她的父亲》的那位名作家,此文使我惊叹不已。叹的是名作家也竟如此之浅薄,还用自己的浅薄,任意造出许多令人作呕的形象。(我因此怀疑我们画家们是否也在做此勾当。)
高缨 著《早辞白帝彩云间》
我当然不必理会,因为他写的不是我。但毕竟不舒服,因为知道他是想写我。大概上帝在安排我的命运时,有这么一个部分,总是让我倒霉。总是这类事,去他的!
……
思聪1,21[1983]
文蔚:
……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美术》上有一篇李永存的文章值得一读。作者是星星美展成员,笔名:薄云。本来许多常识的问题,多年来却搅得稀里胡涂,还要搅下去。你们记者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我也为你担忧。我算不算“持不同政见者”,我不知道。我似乎没有什么政见,只有担忧,为我的祖国担忧。地球仍在旋转,世界仍在进步。我们都向往进步,非常向往。
没有时间来,通通信也好,对吧?
祝好。
思聪1,21[1981]
文蔚:
……
冯国东的文章我读后也很感动,我原以为他那些难以理解的作品,是故弄玄虚,是无病呻吟。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我第一个感想是:我自己太顺利了。
1981年第2期《美术》发表冯国东的文章及作品。
我仍然不能喜欢他的画,他明显的是受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我这方面的知识太贫乏。另一个原因我以为是性格方面的,媚俗无疑是不好的,我希望我的作品人们能理解它,从而唤起人们的感情共鸣。相比之下,我当然喜欢罗中立的《父亲》胜于冯国东的。艺术作品当然要抒“我”之情,但不能以“我”为中心。我这说法是否不公正?不知道。冯国东有他不少的观众,也就是“读者群”,有人喜欢他的旋律和节奏。
……
3月15日思聪[1981]
文蔚:
……
告诉你,会议期间我听到一些对我的最近的作品的反映。有些人劝我修改画中的形象,认为太丑了。持这些看法的多是五十年代的大师兄、师姐。而六十年代的就不同了。他们说:不要听他们(指上面意见)的,就像现在这么画下去。韩美林(知道这人吗?)就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同意后一种,美术作品不一定都是通过直观美感收到效果。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是能入画的,而且更能发人深思。
这次会上不少担任地方领导职务的理事发言中多指责《父亲》一画是“丑化了社会主义农民”。“手上黑黢黢,这种愁苦的形象,还拿到巴黎展出,给中国农民抹黑”。他们觉得《父亲》给他们丢了面子。真是地位不同,感受就不同。
1981年第一期《美术》封面刊发罗中立油画《父亲》。
我看了《父亲》以后,发现感动我的,正是那些“抹黑”的描写。饱经辛酸的皱纹,含愁的善良的眼睛,污秽的手,那代表贫困的粗磁碗……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祖国,灾难深重,至今她仍然贫穷落后,但她毕竟是我的祖国,我的父亲,我不会因为他手黑而感到羞耻,因为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刚刚还在泥土中滚爬,为子孙操劳。这样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资格到巴黎?他们的父亲有汽车、别墅,我的父亲没有,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更有价值的:那些口口声声不忘本的人,因为要那可怜的面子,可以舍弃艺术的真实。这就是“为政治服务”吧,可怜的政治。
……
思聪7,8[1982]
文蔚:
看来,我要是不写,你决心不写给我了。这是我今天早上睁开眼睛突然明白的。
这些天,我的魂依然在凉山飘荡,就在那低低的云层和黑色的山峦之间。白天想着他们,梦里也想着。我必须试着画了。当我静下来回味的时候,似乎才开始有些理解他们了。理解那死去的阿芝,理解那孩子的痛苦的眼睛,理解那天地之间阴郁的色彩。他们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愚昧、迷信,有时样子还使人害怕,他们过着和畜牲一般无二的日子。但他们是诗人。他们日复一日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们的目光,他们踏在山路上的足迹,都是诗,质朴无华的诗。文蔚,你相信吗?诗不会在那漂亮的卫生问里,也不在那照相机前的扭捏作态里,那里是一片空虚啊!
周思聪《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中国画,103x103cm,1982年。
欢乐很容易被遗忘,而痛苦就必然会划下一个痕迹,永远留下了。在我还是“单纯得透明”的年纪时,有人曾批判我“有阴暗的心理”,当时我吓坏了。难道我是怪物?可是这“阴暗的心理”总使我看到那些不该看的阴暗面,我天生就喜欢悲剧胜于喜剧。越是看到我的国家的苦难,我越是爱她,离不开她。
你愿意看我的速写,以后给你看。我不想让你的同行看,他们只会觉得丑。
来信!
思聪11,19[1982]
文蔚:
……
《美术》第7期见到了吗?上面有一页整版介绍了我们的画册,并且故意登出了“有问题”的画。这期的主编栗宪庭胆子不小,是年轻人。不知你注意过没有,《美术》是轮班主编的,总是一期有劲,一期没劲,十分分明。有冯国东等文章的那期也是栗宪庭主编的。当然也招致不少指责甚至痛斥。不过美术界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是支持他的,这样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语,有说《美术》办得糟的,有说办得好的。
7期上还有一篇郎绍君的文章,谈两条借鉴之路,他的观点我很同意。
……
关心《矿工图》的人忽然说起来了。
思聪8,4[1982]
文蔚:
……
甘南有一个刊物叫《当代文艺思潮》,八三年第一期有一文章——《崛起的诗群》。真好!此文使权威人士大为震怒,正组织批判。也许你已读过。此文章使人振奋。
……
思聪83,8,2清晨左笔
文蔚:
……
因为眼睛的问题,书读得极慢。这样倒也好,慢慢咀嚼个中味。钱老先生实在渊博,他引的许多典故,我都没有读过,体味就差了许多。
九一年第一期《江苏画刊》你能看到吗?里面有对我的评论(他们还没有寄给我,但文章我早看过了),你看后告诉我感想如何。还有一个访谈录,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清楚。《江苏画刊》是自去年以后保留下来的极少的美术刊物之一,一向比较活泼,曾等过李小山的文章,现在处境也很微妙,但仍顽强的存在着。
春天又悄悄向我们走近了。这回能留驻几天吗?或许。
戏谈:有人说,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这样生活。
思聪91,2,5
——月雅往期经典,点击以下链接直接阅读——
宋代折枝花鸟画构图程式剖析石涛的伟大与媚俗
悖论董其昌:大师、淫棍和恶霸?
“西泠八家”篆刻印石128方原印照【珍藏版】
金农 | 精品《人物山水册》 《二湘图》,亮瞎你的眼
齐白石早年《花鸟册》(老舍旧藏)
十八岁的千里江山图,流传千古的绝唱,每一部分都是一副经典的山水画
看了陈巨来的原石印,你才知道印章到底有多美(高清组图)
不会被遗忘的大家——忆学仲先生(附高清作品集)
李鳝 |《花鸟册》百图详解
八大山人的心路历程 石鲁 | 写生册
国人看不懂当代水墨,就是不懂艺术么?
美的极致!——敦 煌 手 姿(600势)
敦煌早期彩塑的犍陀罗影响繆谷瑛 | 百 花 图 集
巨献 | 815张高清大图带你走进《清明上河图》中815个人物造型细节
黄宾虹“写”出来的花鸟 (200图) 赵之谦印面60方,美醉了!
盈盈水间,脉脉不语 | 中国画中的水
陆俨少图式梳理——含陆俨少先生最全的写生作品
沉默的大师! 去世七年后作品公诸于世,震撼整个中国画坛(附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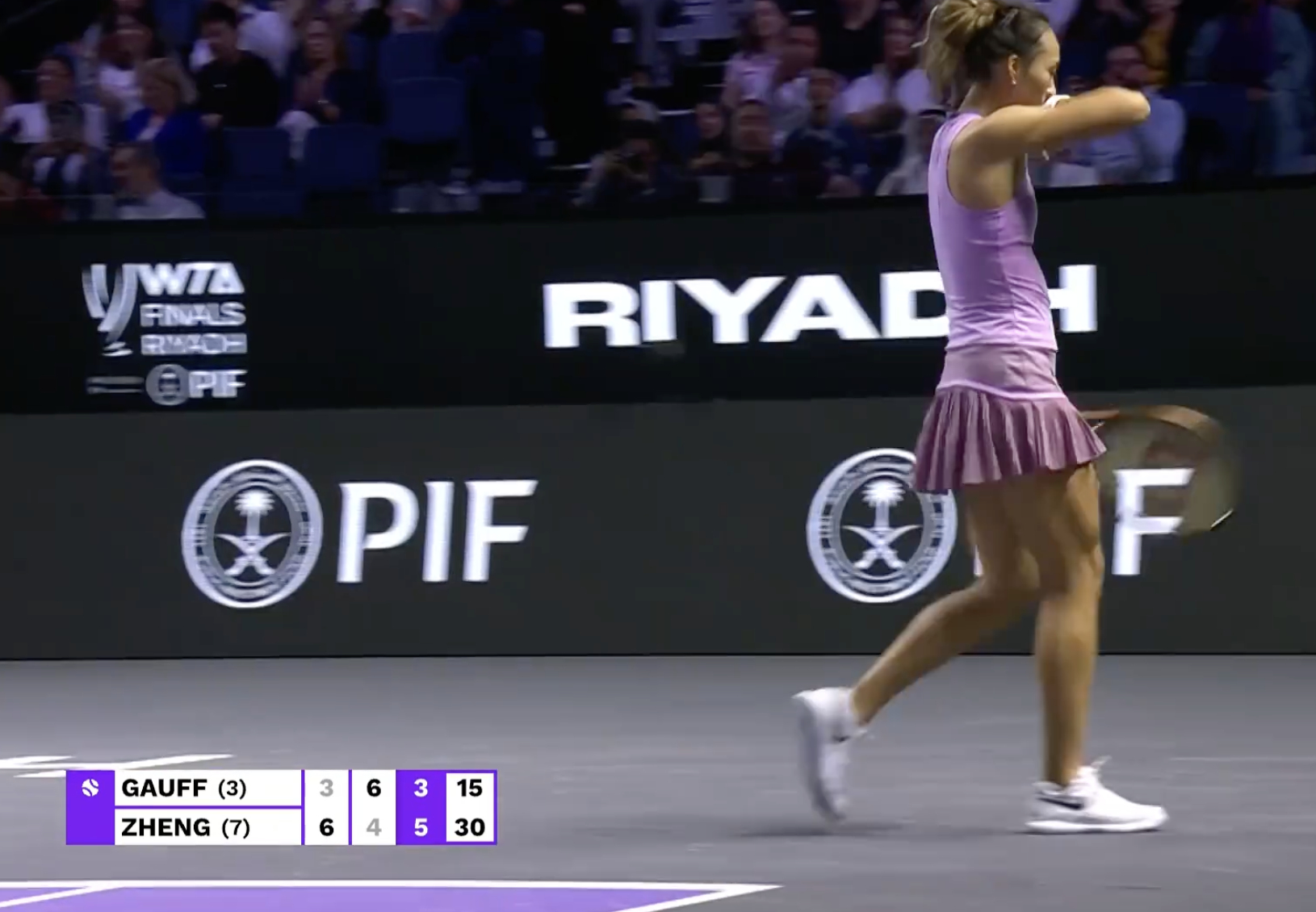





李军欣
回复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用起来非常顺手,强烈推荐给大家! 性价比很高,用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问题,点赞!
韩娜玲
回复已经多次购买了,一如既往的好,值得信赖的商家。 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用起来非常顺手,强烈推荐给大家!
马红楠
回复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n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Highly recommend! Fast shipping and great customer service. Very happy with my purchase.